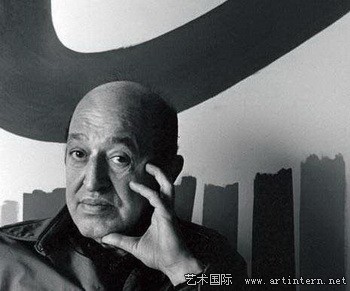|
高名潞:当代艺术史从何时开始?时间:2018-02-13 当代艺术从何时开始?它的起源主要由什么特点决定?或者说,如果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为自己描述了一个哲学宣言,那么当代艺术的哲学是什么?甚至,不少人问,在终结论和后历史主义之后,当代艺术还有哲学吗?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暂且放到一边,首先来看看西方当代艺术史书写是如何为当代艺术分期的。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当代艺术的哲学起源。目前西方学者对当代艺术的分期主要有三种意见。 1945年,战后分期 第一种分期,当代艺术始于“二战”结束的1945年。这是目前最为陈旧,但是在欧美广为接受的说法。很多当代艺术史的名称都采用了大同小异的“194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 since 1945)”做标题。 此外,二战结束后的冷战立场似乎是1945年以后的当代艺术的重要参照和标准。战后当代艺术实际上仍然是西方(或者欧洲)现代艺术史的延续。在80年代以来发表的诸多“1945年以来的艺术”的教科书中,这个时代被看作一个新的艺术史时期,就像它之前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一样,只不过很难象这些流派一样用一个什么“主义”为这个新时期命名。这种视角是最初战后当代艺术叙事的主流,最典型者为劳伦斯•阿罗维(Lawrence Alloway)撰写的《1945年以后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即“战后艺术史”的著作。阿罗维是首位力图为“战后艺术”的崛起找到充分理论和观念依据的首位重要的艺术史家。90年代以来,在英语出版物中,他又陆续发表了多种“194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的专著和教科书。[1] 显然,这些以欧美为中心的1945年之后的艺术史中,战后艺术仍然是战前现代主义的延续。美国的战后抽象表现艺术成为主流叙事。它讲述了战前的欧洲抽象主义是如何转化为另一种国际主义的(即美国式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后者随之成为战后艺术史的主要价值系统。[2]“当代”在这个叙事中意味着对战前现代主义的承接和异变。基于此,“二战”后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以及50年代后期出现的极少主义)被归入“后形式主义”(post formalism),早期抽象主义是形式主义。 近年的重要出版物《1900年以来的艺术》是由《十月》小组的四位艺术史家——福斯特、克劳斯、布瓦和布赫洛撰写的。这本书也把20世纪分为战前和战后两卷,实际上就是现代和当代的区分。但是,作者否认这种断裂性,声称这样分期乃是为了符合学院艺术史教育的现状。同时,作者试图让主题、观念和流派穿越不同的时期,甚至那些决定着艺术作品产生的几种方法论:1.心理分析学;2.艺术社会史;3.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4.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按作者所说,也可以打破前后时代界限,贯穿战前和战后的艺术史之中。所以,为力求客观,此书以历史事件,即每年发生的重要艺术事件为线索来展开作者的20世纪艺术史叙述。[3] 这似乎是合理的叙事角度。比如,杜尚、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也是“二战”前的现代艺术现象,但是在诸多“1945年以后的艺术”的叙事中,人们更愿意把这些战前的前卫流派视为60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特别是观念艺术的直接起源。这个脉络则构成了形式主义逻辑之外的另一个前卫历史逻辑。这就是许多欧美批评家和艺术史家所津津乐道的老前卫和新前卫,或者“二战”前的正统前卫(canonical avant-garde)向战后“新前卫”(neo-avant-garde)的转化历史。
图1. 马塞尔·杜尚《下楼梯的裸女二号》油画,1912 然而,东欧和苏联以及非西方的战后艺术当然被所有战后艺术史排斥在外。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对立面被笼统地冠以“集权主义”艺术,并自然地与希特勒纳粹一起被划入集权艺术阵营。[4]然而,“二战”是反法西斯阵营战胜反人类阵营的有关人类基本道义的战争。这个战争对人类生存的意义远远大于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文化之间的对立,甚至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意义。“二战”期间和战后,在东欧、苏联包括中国都出现了很多表现民众反战、反腐败的批判性的大众传媒艺术,比如,在中国,就出现了很多漫画、版画、年画和招贴等生动的反战艺术。但是如何把这部分艺术纳入一部非冷战叙事的全球现代艺术史之中则是一个颇具挑战、迄今为止尚无人尝试的课题。 比如,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对全球现代文化的影响的角度看,西方现代艺术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艺术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格林伯格早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是托洛斯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个影响分裂为两个阵营,社会主义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两个阵营中的激进者都宣称自己是先锋或者前卫。然而问题是,除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原因之外,是否还有来自道德、文化和传统方面的诸多其他原因?比如,这两种先锋似乎都具有启蒙思想的影响,启蒙和革命乃是两种前卫的都怀有的内在情结,尽管他们面对的可能阶层不同——一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精英,一个是无产阶级大众。为什么会这样?启蒙的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二者那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些都需要超越冷战视角,或者阵营视角去研究。 在西方战后艺术史书写中,一些艺术史家试图为“战后”,或者“冷战艺术”寻找思想理论的根据。有人说,战后艺术起源于一种“冷战美学”(Cold War Aesthetic)。这个美学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现代主义的政治美学,其代表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波洛克和罗斯科(Rothko),他们是美国英雄和现代人(Modern Man)的代表,他们的抽象形式被看作心理学意义上的西方中产阶级“自由世界”的再现,是“波希米亚人”的当代冷战版,他们的艺术“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人性钳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波洛克表现了现代人,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大众有能力自由地表现西方社会中作为个体对社会异化的反应和批评,甚至通过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宣泄来抒发自己的理念,这种自由表现,因此可以视为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那种非理性的专制基础的讽刺,所以,波洛克和罗斯科的艺术表达了欧美“新自由知识分子”(new free intelligentsias)的声音。[5]因此,很多西方艺术史家认为,格林伯格的前卫和现代绘画也正是在这个“冷战美学”上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性艺术标准。
图2. 马克·罗斯科《No. 3/No. 13》油画,1949 这样看来,1945不仅仅是一个西方艺术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全球冷战艺术的起点。冷战促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艺术上的道德分水岭。 然而,对于东欧和苏联阵营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被看作一种比资本主义的现代艺术更加当代,即更加进步的艺术形式。比如卢卡奇就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卢卡奇把它称为“当代现实主义”(contemporary realism),因为它抓住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本质。西方现代主义则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是人性异化的再现,因此现代主义再现了错误的历史时间。[6]卢卡奇有关文学艺术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中的物化理论之上。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引申出艺术反映现实真实的理论。卢卡奇认为,艺术最重要的功能是反映真实。然而,这个真实不能仅仅从局部的、分裂的、个别的和表面化的角度去理解,相反必须要从“总体”的角度去理解。他所说的总体是指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这个“总和”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过程再现出来的。 卢卡奇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意识的来源入手,展开他的文艺理论的阐述。商品拜物教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体现,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恰恰失去了认识商品中所凝结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商品交换导致普遍性的物恋,物恋则遮蔽了商品生产的基础,不平等的人性,即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所以,现实的真实必须从认识这个商品拜物教的神秘性(物恋)是怎样形成的,从形成物恋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出发,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社会和现实的真实性。[7]正是从这一点,卢卡奇批判了资本主义艺术的形式主义,它的颓废主义和精神分裂的特点。尽管现代主义也可能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或者说,如果说现代主义中也具有某些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积极性的话,它也只是再现了它的精神分裂的症状,并没有指出其病因,它没有也不可能洞彻资本主义的本质——商品拜物教和人的社会关系之间的深层原因。[8] 应该说,卢卡奇的批判是深刻的。然而,这个深刻性批判却既没有在资本主义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中生效,也没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真正出现。卢卡奇的深刻性如果发生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内部,而不是发生在现代艺术的外部对立的一方,比如,我们设想,卢卡奇是一位生活在西方的现代艺术的批评家,而不是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局外”立场,那么,他的批判有可能会更加深刻和有效。 其实,自杜尚以来西方的反体制观念艺术已经认识到了这个商品拜物或者马克思所说的“物恋”的本质性危害,但是,这个批判总是无效。第一,由于启蒙以来的美学独立以及艺术和社会的二元分离性,以及前卫的布尔乔亚出身注定了它的反叛是象牙之塔和语言学的,即在美学自律性的范围之内的批判。[9]这个自律性的批评实践被充分地体现在格林伯格的现代艺术批评中。他在《前卫与媚俗》一文中已经指出了现代艺术家的布尔乔亚阶级出身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体制的局限性,最终还是会成为市场的追逐者。但是,格林伯格关注的是现代艺术的精英价值,它的语言自律的平面性价值。所以,T.J.克拉克指出,格林伯格应当把平面性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接起来,不应该把“平面性”置于社会结构之外。然而,克拉克的阶级观点也没能走多远,他只能把资本主义的阶级性与资产阶级生活中的微观片断对接,即景观再现,以此去解释经济现实和资产阶级生活之间的符号化对等关系。
图3. 格林伯格 第二,由于现代主义艺术系统仍然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一部分,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最终不能逃脱其商品价值的归宿,遂导致商品拜物教的恶性循环,因此,早期抵制资本体制的前卫最终沦为妥协性和折中的新前卫,甚至“后新前卫”(post-neo-avant-garde),其代表性人物就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
图4. (英)达明·赫斯特《献给上帝之爱》白金钻石骷髅头骨,2007 达明·赫斯特的钻石头骨作品《献给上帝之爱》是在母亲的一句话启发下制作的。赫斯特的母亲问儿子:“为了上帝之爱,你能够做什么?”(For the love of Go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作品的尺寸为真人头盖骨等大,用白金和8601个上等钻石制作,售价 1亿美元,创下在世艺术家作品售价的最高纪录。[图4]且不说这些钻石的镶嵌是委托珠宝店而非赫斯特本人亲手完成的,就作品所使用的价值连城的材料本身来说(造价2800万美元),也不是一般艺术家可以负担得起的,连赫斯特本人都担心它可能过分炫耀了。赫斯特作品的制作更像是投资行为,是由艺术家、他的代理白立方画廊及其经纪人邓菲(Frank Dunphy)共同策划的。实际上,正是在遇到经纪人邓菲之后,赫斯特才开始从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变成商业奇迹,经纪人不仅帮助赫斯特建立工作室、与画廊谈判,还建议赫斯特将他经营的一家倒闭餐厅的用品进行拍卖,最终这些署名“赫斯特”的餐厅用品在伦敦苏富比拍出了两千万美元。赫斯特因此从他艺术生涯的一开始就决定扔掉此前所有前卫艺术家,不管是老前卫还是新前卫们对市场暧昧和羞答答的姿态,公开宣称自己的艺术哲学是把艺术创作与商业体制融为一体。商品等于上帝之爱,这可能就是赫斯特《献给上帝之爱》这件稀世作品的注脚。所以,“后新前卫”直接把商品拜物教奉为艺术的本质和崇拜对象,不像杰夫•昆斯(Jeff Koons可能是最典型的新前卫艺术家),仍然把如何通过反讽去再现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媚俗趣味作为自己的目的,用商品的媚俗形式去调侃当代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媚俗本质。作品《兔子》的灵感来自于玩具店的充气玩具,然而昆斯采用了与轻盈的充气材料相反的、厚重的、有镜面反射效果的不锈钢,隐喻着深受教堂和有钱人喜爱的、亮闪闪的、有银器质感的材质,反讽了充斥着华而不实的奢侈品的消费社会。通过对中产阶级趣味的模仿,昆斯的作品反映出当代艺术(或者说后现代艺术)的一个转变,即当代艺术不再是对商品社会的拒斥和尖锐批判,而是对消费社会的迎合,透露着对无处不在的商品气息的讨好[10]。[图5]
图5. 杰夫·昆斯《兔子》不锈钢,1986年 另一方面,尽管卢卡奇也强烈反对苏联社会主义艺术变成政治的传声筒的倾向,但其深刻性也并没有促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对自身的深刻反省,甚至,卢卡奇的理论一度被苏联官方批评为修正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简单批判并没有促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对本身仍然带有的、我称为“先天性资本遗传基因”的社会机制的警觉和反省。因此,卢卡奇的“总体性”的历史观本身可能存在着总体性的盲区,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在社会主义机制中也存在的资本遗传基因,这个基因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机制中显而易见。这当然是历史的局限性。在卢卡奇时代,他还没有办法看到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比如,中国当代艺术经过20年的市场化之后,正在严峻地面临着西方当代艺术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同样问题,甚至更加严峻。[11] 中国当代艺术的特点、逻辑和价值是什么?或许我们不能像卢卡奇那样站在一个局外立场,比如只是从资本主义体制的角度看待社会主义的当代艺术。反之,也不能仅仅从自身的体制局限看自身(无论是当代还是传统),必须从一个“总体性”角度审视中国的和西方的当代艺术。没有这个总体性就很难判断中国当代艺术。那么,这个总体性(或者我们所说的“整一性”)的历史观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专门探讨,但至少我们可以在目前既有的战后西方艺术史中,无论是以1945年为起点的,还是更晚期起点的当代艺术史书写中可以发现,它们似乎都缺乏一个对那个与西方主流对立的“他者”,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代艺术的描述,因此造成“他者”在“世界”(实乃欧美)现代艺术史中的非存在和缺席。这个排斥将注定使这些艺术史不全面(不整一),缺少了作为世界整体的另一个“他者”的描述,注定会让“自己”显得不完整。 当然,人们可以说,只有1945年以来的西方艺术是当代艺术,其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不是当代艺术。这个说法,应该说似乎容易得到共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回到格林伯格的当代标准和卢卡奇当代标准中去争论。或者回到形式自律或者道德自律的标准去辩论这个问题。 1960年代分期 第二种分期认为,当代艺术从60年代开始。这种分期认为,1945年的分期是冷战及地缘政治的产物,而且带有明显的早期前卫的怀旧意识和欧洲艺术史逻辑的封闭倾向。[12]所以以60年代分期的历史叙述,则更加专注于这个时代出现的那些活跃的艺术运动本身,特别是自从60年代初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行为艺术、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的实践,以及艺术系统对这些艺术实践的反应和推动作用。[13]另一方面,60年代也是一个以美国当代艺术为标准的准国际化的时代。比如,南美洲六七十年代的艺术、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的艺术都受到了美国的深刻影响,日本的“物派”和日本建筑的“新陈代谢派”都是60年代出现的,它们具有东方哲学意味,但总体上可以看作是达达和美国观念艺术的东方版。[14] 这种“国际化”显然与60年代的国际政治有关。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60年代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遍布欧亚的示威和工人运动……60年代的世界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然而极有意义的课题。但是,迄今为止,这段艺术史却仍然被描述为以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观念艺术为主线的叙事历史,从极少主义到概念艺术和大地艺术的历史。所以,有的理论家把这段当代艺术叫做“后观念艺术”(post-conceptual),并将它视为当代艺术的特点和起源。[15]这个后观念艺术的特点是与之前那些建立在媒介视觉进化论基础上的艺术理论发生了断裂。这个断裂为引进无限可能性的视觉媒介,特别是为大众媒介(印刷和照片复制)以及现成品进入艺术打开了大门。表面上看,60年代的观念艺术打破了媒介美学的局限性,让艺术材料和媒介选择更加充分自由。其实,其本质在于,它把艺术推向了意识形态叙事,即社会观念的极端。“后观念”的意思,因此可以简单地界定为,“美学观念之后的政治社会观念”。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后现代以来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语言学”的兴起。 其实,这种所谓的“后观念”声音最明显地反映在70年代的文化和现实政治之中的关系之中,而不仅仅是60年代的政治运动自身。只有到了70年代,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政治,比如女权主义、多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风起云涌,对文化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所以,有的艺术史家更倾向于把当代艺术的起源追朔到70年代。[16]因为70年代是北美兴起的观念艺术从艺术本体质询走向体制批判的转折时期。60年代末的观念艺术仍然钟情哲学,比如“艺术与语言”小组(art and language)仍然主要关注形象和概念的关系,即概念对形象的整合作用等。这实际上仍然是西方一些理论家所说的现代主义的媒介进化观念的再延伸。比如,语言小组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格林伯格所追求的平面媒介的深度性和隐藏性的继续,因为深度和隐藏都指向概念。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先声。极少主义把抽象艺术的媒介性推到了极端,它表明战后的“后形式主义”(post-formalism)已经走到强弩之末,“抽象”变成了只是类似打格子一样的图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任何乌托邦可言。另一方面,60年代的观念艺术把格林伯格的抽象语言的概念化能指的功能推向了极端,推向了那个启蒙以来所主导的“形象—概念”那个“钟摆”的另一极端,即它的概念一端。
图6. (荷)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版面油画,1942-43 到了70年代,观念艺术把“概念”延伸到体制观念,某种程度上回到了杜尚。一批艺术家,比如汉斯•哈克等把作品内容与美术馆的项目、它们的资本赞助背景以及项目资金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等作为艺术作品的直接内容。汉斯哈克等人的作品可能对于奥斯本等西方理论家而言,是70年代以后最具批判性的和最具第三世界“反帝”意识的西方艺术家了。然而,我们认为,这个“反帝”其实不是现实政治中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反帝,它仍然是杜尚以来的反体制,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机制的讽喻批判。但是,正是这个意识形态倾向开启了90年代开始流行的当代视觉文化中的“语言政治学”(semiotic politics)倾向。悖论的是,这种语言政治学在概念和图像的二元论中,把当代艺术带向了“图像转向”:最大程度地解放“图像”的语词功能和为政治学的逻辑和“概念”服务的自由。图像和语词这个再现理论的核心二元概念于是在文化政治语言学的阴影下达到了空前的统一。所以,我认为,这是以1960 年代,即西方观念艺术兴起为起点的当代艺术史书写的合法性所在。 1989年分期 第三种分期是以1989年为当代艺术的起点。这是最近的,同时也是最为流行的看法。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这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称之为“三个世界的终结”,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倒塌,没有了第一世界这回事,从此开始了全球化政治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从欧美和苏联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冷战转入以民族国家和多元文化冲突为特点的全球政治。[17] 伴随着这个全球化政治而来的是覆盖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neoliberal economy)。美国里根时代大力推出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政策,90年代以后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动力,包括像中国、印度等这样的国家,也都向这种市场经济转型。[18] 有的批评家认为,以1989年分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卫艺术”赖以生存的历史立场不复存在。那个讲究质量的艺术自律被融入批量的、市场化的文化产业链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以往那个支撑着西方现代主义以来的“前卫”彻底面临危机。20世纪上半期的前卫艺术总是自觉地保持着某种历史意识,或者一种具有艺术史意识的、从美学独立的角度不断应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前卫意识。但是这个具有历史意识的前卫精神自从1989年以后(严格地说可能更早,自从1960年代以来)遇到国际展览中大量出现的多样化作品的直接挑战。这些作品一般不再强调那个历史前卫的独立性和自足逻辑,抛弃了美学自律并转移到体制批判。因此,这些在各种国际双年展中出现的作品,大多强调个人经验和反历史的角度。因此从美学上,他们不再追求完整,而是分散的和非凝聚的反美学观念。[19]它们的内容可能是政治的,他们的语言是反美学的,但这里的政治题材和反美学的统一正是当代艺术流行的文化政治语言学模式的最大特点,然而它与政治现实毫不相关。 如果把反美学或者反美学自律的源头回溯到60年代的观念艺术,那么主张以1989年全球化出现作为当代艺术史开始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观点。即,只有到了全球化时代,到了无处不在的文化产业时代,美学自律才彻底失去存在意义。比如,奥斯本就把60年代的反美学与1989年以后的全球经济、跨国文化产业连在一起。并且用“呲实的文化”(confirmative culture)这个概念去描述这个新出现的跨国艺术产业(transnationalization: art industry)。这个新的艺术系统不是反自律,而是把艺术自律俘虏了,让它变成这个跨国文化产业的国际语言的一部分了。[20]显然,把达明•赫斯特作为这一部份的代表则是最合适和最有说服力不过了。 以1989年分期的观点还把目光投向全球化和市场化给当代艺术带来的冲击。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笼罩下的当代艺术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现象。国际双年展和艺术博览会风靡新型经济体地区。对于这些双年展,国际上通常认为上海双年展和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仍然是西方双年展形式的延伸,而哈瓦那、达喀尔和开罗双年展则被认为是在西方艺术之外另辟蹊径的双年展,因为后者更重视区域特性和历史传承。然而不论怎样,这些双年展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吸引了大量的收藏家、策划人、出版商和翻译家,他们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艺术自身,而在于把全球的艺术机构和艺术职能人员编织在一起,使他们更为方便地为呈现全球化的艺术现实而工作。这是21世纪开始形成的一种新的、更为全面的全球化体制(world institutionalization),或者被一些人称为当代艺术的“一体化样式”(hegemonic formation)。[21] 也有人将数码虚拟作为当代艺术的主要特点,同时也是1989年分期的另一个标志。当代科技和互联网等是以往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表达手段,数码虚拟似乎可以把过去和未来联在一起,把真实和神话结为一体,可以把原始和现代共时性地构成一个世界,就像电影《阿凡达》呈现给我们的虚幻世界那样。在理论上,如今方兴未艾的图像理论(pictorial theory)正在把这种数码科技的图像魅力和铺天盖地的通俗大众媒体的视觉效果整合在一起,把它称之为当代艺术的新纪元,以替代之前的各种艺术媒介和理论。
图7. 电影《阿凡达》的海报 总之,我们看到上述的三个分期有某些共同点。首先,当代艺术的分期都来自政治事件:第一种分期,二战结束和冷战开始;第二种分期,60年代的国际性政治风暴;第三种分期,1989年苏联、东欧解体。其次,三个阶段的艺术运动纠结不清,从艺术史的角度,都把观念和观念艺术放在中心位置,也就是说,观念(concept)是所有这三个分期的叙事主线:1945年分期论是以“观念化了的媒介”,即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开始的;1960年的分期论则是以摆脱媒介美学并转而寻求概念美学的观念艺术开始的;1989年分期论则试图以完全摆脱美学的“大观念艺术”或者“后观念艺术”(全球化、双年展化和数码化为标志)的兴起为当代艺术的起点。而这个“大观念”艺术的理论基础则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视觉文化理论。这个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语言学的色彩,因此西方当代艺术在80年代以后,名正言顺地超越了此前的以艺术史美学为基础的“观念艺术”,进入了以文化政治语言学为核心的“大观念艺术”阶段。西方的当代艺术书写对非西方包括中国的当代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我们愿意把中国当代艺术植入这个西方逻辑之中,或者试图寻找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逻辑,我们都必须首先从对西方当代艺术逻辑的梳理、认识和反思开始。 【注释】 [1]阿罗维的重要著作包括:Lawrence Alloway, Topics in American Art Since 1945, Norton: 1975;"Art in Western Europe: the Postwar Years, 1945-55," in Network: Art and the Complex Present, U.M.I., 1984, ch.4;此外,尼克•斯丹格(Nikos Stangos)在1981年发表的《现代艺术观念》(Concepts of Modern Art)一书也非常重要,它虽然是一本有关现当代,或者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艺术史著作,但此书是按照不同流派和运动的顺序编写的。尽管也包括了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艺术流派,但是主要从“主义”的角度讨论现代艺术,包括战后艺术的观念和理论宣言,Nikos Stangos, Concepts of Modern Art,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而保罗•伍德(Paul Wood)等人主编的《遭遇抗辩的现代主义:四十年代以来的艺术》则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审视现代艺术的各种“主义”。(Paul Wood, et, al. Modernism in Dispute: Art Since the Fort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阿瑟·麦维克(Arthur Marwick)在2002年发表的《1945年以来的西方艺术》把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作为战后西方艺术的起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转折作为主要的议题之一,法国五月风暴及之后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作为艺术史叙事的理论基础。(Arthur Marwick, The Arts in the West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丹尼尔•惠勒编写的教科书《世纪中以来的艺术:1945年至今》是一本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非常实用的印有大量图片的教科书,秉承典型的正统观点,把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作为战后艺术的开始,并把战后艺术的源头追溯到世纪初的现代主义(Daniel Wheeler, Art Since Mid-Century: 1945 to the Present, Prentice-Hall, Ind., 1991);从冷战美学的角度讨论1945年以后西方当代艺术发展流派的代表作之一是由达维特•霍普斯金撰写的《现代艺术之后:1945-2000》一书,这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当代艺术史的教科书(David Hopkins, After Modern Art: 1945 – 2000 , Oxford, 2000)。 [2]这方面的著作可参见Michael Auping, Abstract Expressionism: The Critical Developments,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87. [3] Rosalind Krauss et al., Art Since 1900: Modernism, Antimodernism, Postmodernis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5. [4] Igor Golomstock,Totalitarian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Third Reich, Fascist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Overlook Hardcover 1990. [5]David Hopkins, After Modern Art: 1945 – 2000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11. [6] Peter Osborne, Anywhere of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 London,New York:Verso, 2013, p.18 [7]Karl Marx, “The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Capital (1867), I, pt. 1, ch.1, sec.4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IV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52-68页。 [8]Georg Lukás,“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riat,”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first published in 1923),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gde:MIT Press, 1972, pp.83-110. Georg Lukás,“The Ideology of Modernism,”in David H. Richter,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Bedford/St. Martin's, 2006, pp.1218-1232. [9]比如,比格尔的Theory of Avant-Garde (《前卫理论》)中对卢卡奇的讨论,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比格尔认为,卢卡奇的资本主义批判是现实参与,但比格尔认为文学理论的批判应该是中立性批判,而不是卢卡奇的干预性批判。我们理解比格尔的这个中立性主要是指建立在语言学自律理论之上的批判。 [10]Haim Steinbach, Jeff Koons, Sherrie Levine, Philip Taaffe, Peter Halley, Ashley Bickerton, “From Criticism to Complicity”, in Charles Harrison and Paul Wood ed.,Art in Theory 1900-1990,An Anthology of Changing Ideas, p.1080. [11]于是,这让我们想到,应该怎样界定中国当代艺术?这似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如何建树而不仅仅是建立在模仿西方当代艺术的角度,而是建树一种既有历史逻辑也有当代经验的当代中国艺术模式?或许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正的本质所在,否则,它或许只能被看作西方20世纪以来的老前卫、新前卫或者后新前卫在一个相异的社会主义中国体制中的简单复制和翻版。 [12] Peter Osborne, Anywhere of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p.19. [13]几篇有关激浪派、行为艺术和观念艺术的文章见:HarryRuhe, Fluxus: The most Radical and Experimental Art Movement of the Sixties, Amsterdam: "A", 1979;Susan Sontag, "Happenings: An Art of Radical Justaposition,"in Against Interpertation and Other Essay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1966, pp. 58-70;Thomas McEvilley, "I Think Therefore I am", Artforum, (Summer, 1985), pp.174-203. [14]镰仓画廊出版《物派》,Mono-ha, Kamakura Gallery, Tokyo,1986 ; Lee Ufan, “Foreshadowing and Premonitions: Mono-ha”, in Mono-ha – School of Things, Kettle’s Yard, 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001, p.21; Michael F Ross, Beyond Metabolism: The New Japanese Architecture, New York: Architecture Record Books, 1978;Simon Croom,Mono-ha – School of Things, Kettle’s Yard, Cambridge 2011. [15] Peter Osborne, Anywhere of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p19 [16]比如,泰勒的著作突出了这个观点。Brandon Taylor,Contemporary Art: Art Since 1970,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4. [17]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最早预示了21世纪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乃至儒教之间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矛盾和对抗(antagonism)正是一种新的整合动力,见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New Political Subjects:Toward a New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Cary Nelson and Lawra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nois Press, 1988, pp. 89-91. [18]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和《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恰如其分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认为它不但是一种比马克思所说的跨国资本主义经济更为鲜活有效的全球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金融寡头、跨国公司、自由贸易和互联网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打破国家界限,从而使资本能够重新转移和积累。 [19] Peter Osborne, Anywhere of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p.21 [20] Ibid,p.162. [21]Alexander Alberro’s response to Hal Foster’s “A Questionnaire on ‘The Contemporary’, in October, Fall 2009, Cambridge:MIT Press, no.130, pp. 55 – 60. 注:本文为《立场·模式·语境——当代艺术史书写》前言,高名潞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